本網訊 曆史因細節而真實可感。一百五十年前德川幕府派遣的首艘官方貿易船“千歲丸”号載着年輕的武士們來到了中國上海,展開了近代中日官方交往的曆史。9月15日上午,在六教213教室,日本神戶女子學院教授宮田道昭再現“千歲丸”号來華兩個月間,來訪武士與普通中國人民的交往細節,拉近了與曆史的距離。韋立新教授與日語文化方向的學子們熱烈歡迎了前來講學的宮田道昭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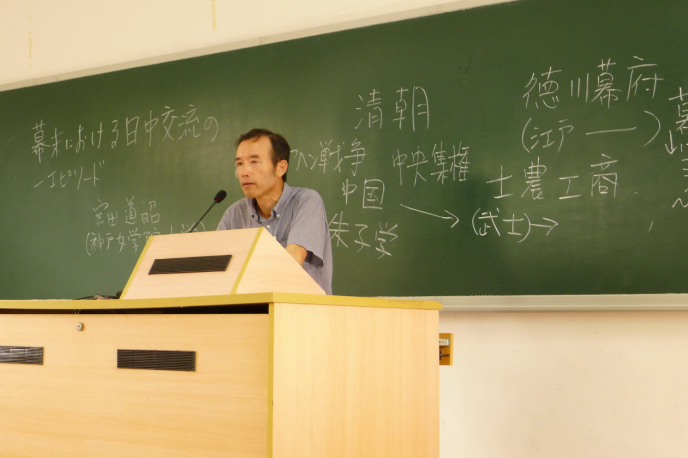
宮田教授認真講課
為了令在場的同學們更好地理解主題,宮田道昭首先詳細介紹了講座主題——“幕末における日中交流の-エピソード”(幕府末期中日交流佚事)的時代背景。他說,隻有學習好、理解好當時的社會、經濟、人們的思想和生活,才能夠理解當今的日本社會以及中日交往的現狀。
據宮田教授介紹,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中,日本和中國中斷了官方交往。直到1862年,即150年前,德川幕府派遣第一艘官方貿易船“千歲丸”号抵達中國上海,這成為近代中日官方交流史的出發點。來華的年輕武士們在中國看到了什麼,思考了什麼,以及他們與中國民衆們是如何交往如何對話的,這些本來在曆史長河中模糊了的細節,通過一百五十年前來華使節團中四個年輕武士的筆記重新變得清晰。宮田道昭教授摘取了其中的一部分,并為同學們重點再現了其中一位武士高杉晉作與當時的一位清朝武官陳汝欽的交往過程。

日語學子專心聽課
這四名年輕的武士分别是:高杉晉作(萩藩,25歲),名倉予何人(浜松藩,30多歲),日比野輝寬(尾州藩,25歲),納富介次郎(佐賀藩,18歲)。在上海的兩個月,日本武士配着刀、穿着和服裙褲在街上走的話,不管在哪裡人們都會圍着觀看,發出爆笑。日比野輝寬寫道:“中國人笑日本人的發髻,日本人笑中國人的辮子,這是文化的差異,而不是哪個更好或那個更美。”中國人笑日本人的發髻,這是因為他們初次見到的緣故,而不是因着尖酸的敵意。
當時,中國正處于内憂外患的局面,而彼時的日本也面臨着美軍艦駛入浦賀港、要求日本開放門戶以及國内幕府與藩對立的困境。日本的武士們與中國的改革家們,如王韬等,都同樣面對着傳統觀念與技術創新激烈沖擊的時代。在“千歲丸”号來訪時,年輕的武士高杉晉作(歸國後創建奇兵隊,将藩内輿論轉化為倒幕的著名人物)在與當時上海縣城一位武官的第二次見面中,即直率地提出了他對中國程朱理學的批判,“中國的朱子先生倡導的‘格物緻知’和西洋的科學技術——鐵造船和大炮有什麼不一樣嗎?”他說,“我們之所以不能造出鐵造船和大炮是因為我們自己的努力不夠。這樣下去的話,雖口唱聖人之言,最終隻會淪為列強的奴隸。”而後他又為自己的言行向陳汝欽道歉,陳評價其就像孔子口中的“吾黨小子”“狂簡”,有大志向,行為粗率簡單。兩人于是引為知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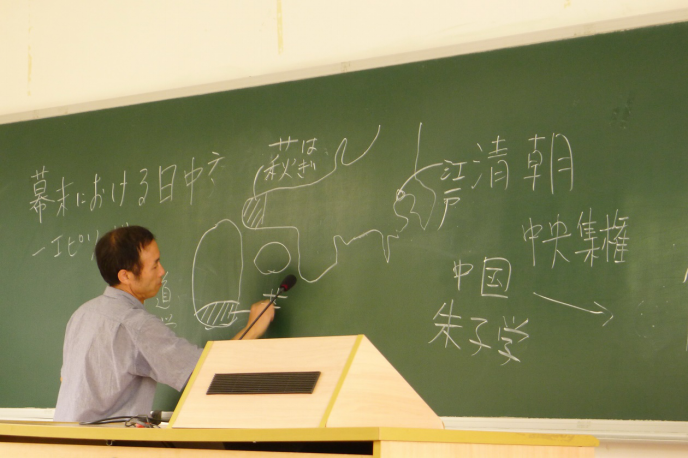
宮田教授書寫“曆史”
宮田道昭将這段細節生動地展現出來,包括兩人初見面時的客氣開場白、互相道别陳向高杉晉作增送字畫時兩人的言行,以及高杉晉作拜托陳汝欽為其取字,改動陳汝欽的字“勉生”為“默生”作為自己的字等細節。看起來遙不可及、抽象不可感的曆史就這樣徐徐在同學們面前展開。
文字:郭美燕
攝影:歐陽雅雯
編輯:邝英華